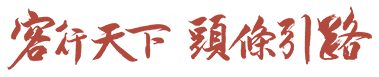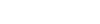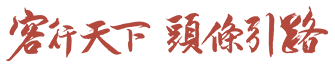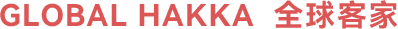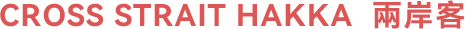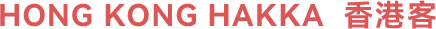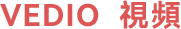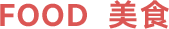客家小暑,除了仙人粄,還是仙人粄

客家小暑,除了仙人粄,還是仙人粄

「小暑過,一日熱三分。」這句話,是我阿婆嘴裡的咒語。一說完,滿山的熱氣便在空中翻滾,蟬叫聲炸裂,像是誰在灶頭丟進了熱油。那年頭,沒有空調、沒有雪糕,只有山邊一種叫「仙草」的東西,能從烈日裡挖出一絲涼意。
那是一碗仙人粄,黑得發亮,涼得透骨,吃進嘴裡像是含了一塊月光。現在我在城市裡過小暑,窗外是汽車的引擎聲,屋裡是冰箱的轟鳴聲,唯一讓我記起老家的,是記憶深處那碗母親端來的仙人粄。

我阿婆說,仙草是天上下凡的東西,長在荒山野嶺,認得它的人不多,熬它的人更少。她的手裡總有一把鐮刀,一只破竹簍。每次她帶我上山,我都跟在她後頭,看着她蹲下來,一手拔草,一手翻土,有時連蛇都給她驚動出來。我問她怕不怕,她說:「蛇怕人,就像熱怕仙草。」
曬乾的仙草,要熬三個時辰。那年廚房還是土牆圍着的,煙從瓦縫裡鑽出來,香氣飄得滿村都是。水黑了,草爛了,整鍋冒出微苦的香氣。我站在灶邊,一邊搖扇,一邊眼巴巴等着那碗會顫的仙人粄。那不是點心,是客家人從泥土裡熬出來的詩。
如今,我在異鄉的廚房裡,重複着母親的手藝。仙草粉是從老家寄來的,現在做仙人粄不像從前這麽復雜,直接用粉末加水慢火煮便可。我站在瓦斯爐前,像站在童年的灶腳邊,看着那鍋水慢慢黑下來,變得濃稠、黏滑。
熬好後,放凉,我舀了一碗,坐在陽台上,一口一口地吃。那苦澀,那甘涼,那一陣子吹來的風,彷彿全世界都安靜下來了。我知道,不管我走多遠,仙人粄都會在那裡,像一口老井,藏着我童年的夏天。
這,就是我們客家人的小暑。
一碗仙人粄,清涼如詩,苦甘如歌。
客家小暑,除了仙人粄,還是仙人粄


「小暑過,一日熱三分。」這句話,是我阿婆嘴裡的咒語。一說完,滿山的熱氣便在空中翻滾,蟬叫聲炸裂,像是誰在灶頭丟進了熱油。那年頭,沒有空調、沒有雪糕,只有山邊一種叫「仙草」的東西,能從烈日裡挖出一絲涼意。
那是一碗仙人粄,黑得發亮,涼得透骨,吃進嘴裡像是含了一塊月光。現在我在城市裡過小暑,窗外是汽車的引擎聲,屋裡是冰箱的轟鳴聲,唯一讓我記起老家的,是記憶深處那碗母親端來的仙人粄。

我阿婆說,仙草是天上下凡的東西,長在荒山野嶺,認得它的人不多,熬它的人更少。她的手裡總有一把鐮刀,一只破竹簍。每次她帶我上山,我都跟在她後頭,看着她蹲下來,一手拔草,一手翻土,有時連蛇都給她驚動出來。我問她怕不怕,她說:「蛇怕人,就像熱怕仙草。」
曬乾的仙草,要熬三個時辰。那年廚房還是土牆圍着的,煙從瓦縫裡鑽出來,香氣飄得滿村都是。水黑了,草爛了,整鍋冒出微苦的香氣。我站在灶邊,一邊搖扇,一邊眼巴巴等着那碗會顫的仙人粄。那不是點心,是客家人從泥土裡熬出來的詩。
如今,我在異鄉的廚房裡,重複着母親的手藝。仙草粉是從老家寄來的,現在做仙人粄不像從前這麽復雜,直接用粉末加水慢火煮便可。我站在瓦斯爐前,像站在童年的灶腳邊,看着那鍋水慢慢黑下來,變得濃稠、黏滑。
熬好後,放凉,我舀了一碗,坐在陽台上,一口一口地吃。那苦澀,那甘涼,那一陣子吹來的風,彷彿全世界都安靜下來了。我知道,不管我走多遠,仙人粄都會在那裡,像一口老井,藏着我童年的夏天。
這,就是我們客家人的小暑。
一碗仙人粄,清涼如詩,苦甘如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