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華教授教你如何跑贏AI:人類有限的註意力該如何分配?

清華教授教你如何跑贏AI:人類有限的註意力該如何分配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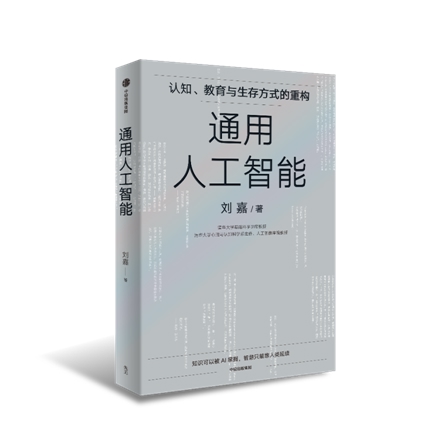
《通用人工智能:認知、教育與生存方式的重構》,劉嘉 著,中信出版集團出版
我們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智能躍遷。人工智能帶來的,遠不止於技術革新,更是一場深刻重塑人類認知、教育與生存方式的範式轉移。
這場躍遷的關鍵,不在於技術會走多遠,而在於人類如何重新認識自我。當知識不再稀缺,學習的意義何在?當智能無處不在,智慧的棲身之所又在何處?當工具變成智能體,人的核心價值又該如何彰顯?
清華大學基礎科學講席教授、清華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系主任劉嘉,站在歷史的交匯點,以獨特的跨學科視角,深入解析通用人工智能的演化路徑與底層邏輯、語言如何承載認知,以及人類能力結構如何在新時代被重新定義。
>>內文選讀
GPT的T,指的是Transformer,其最核心、最精妙之處就是「註意力機製」。它會對一段文本中每個詞語與其他所有詞語之間的關系進行評估,計算出它們之間的關聯強弱程度,從而捕捉信息之間的相互關系,以實現高效而精準的信息處理。所以,學習的本質也是註意力分配的藝術。
我們所處的世界彼此相連,而非孤立隨機。在物理層面,世界由物質和能量組成,它們之間不斷地相互作用,形成復雜而穩定的秩序。在生命層面,物種之間通過復雜的生態網絡連接起來,生態鏈中每個環節互依互存,任何個體的變化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。在人文社會層面,每個人看似獨立,但無時無刻不在通過溝通、情感聯結與社會網絡交織在一起。文明的存續與演化,來源於人與人之間頻繁而有序的互動。
英國詩人約翰·多恩說:「沒有人是一座孤島,可以自全……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損失,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,因此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,它就為你而鳴。」美國行為科學家阿莫斯·特沃斯基也說:「人不復雜,復雜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。」

應當如何分配註意力來認識我們所在的這個世界呢?
第一,註意高質量的數據和人。在機器學習領域,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第一性原理:「垃圾輸入,垃圾輸出。」再多的參數,再強大的算力,如果輸入的數據質量低下,最終訓練出來的大模型也必然表現糟糕。所以,OpenAI在訓練初期便嚴格把控數據質量,選用了維基百科、經典書籍、科研論文、優秀代碼和高質量互聯網內容作為註意力處理的信息。這些精心挑選的材料構成了GPT的認知基座。
截至2024年6月,我國短視頻用戶數量達到10.5億,占整體網民的95.5%,人均每天觀看時長約151分鐘。而閱讀用戶只有短視頻用戶的一半,人均每天閱讀時長只有23分鐘。AI在學習,人類卻在沈迷。
真正與註意力門當戶對的是高質量的數據集和人。在進入某個領域前,首先精心構建你的數據集:誰是這個領域的權威,哪些書、線上課程是這個領域的經典,哪些工具能讓這個領域的抽象知識變得具象清晰?之後,閱讀入門材料快速建立對這個領域的基本認知;接下來,對經典或權威的書籍或教材進行深度學習,建立完善的知識框架;最後,通過專業研究文獻並與專家或AI互動交流,拓寬和深化自己的認知邊界。
第二,註意實例而非規則。符號主義給AI以規則:「如果一個動物有尖尖的耳朵,胡須明顯,並且眼睛在夜間能反光,那麽它是貓。」這時,狐貍、猞猁、浣熊和狼也會被符號主義AI識別成貓。而聯結主義只給AI貓的圖片,各種各樣貓的圖片,讓註意力在海量的數據中主動探尋其中蘊含的模式和規律。前者是授人以魚——人類先提取特征,然後把特征餵給AI,即人類向AI輸入人類學習的結果,AI只需要記憶,正所謂前面有多少智能,背後就有多少人工。後者是授人以漁——沒有工程師總結的規則,只有精心挑選的實例,讓神經網絡自己學習,讓它自己去充分挖掘全部可能,因為「足夠大的神經網絡當然無所不能」(計算軟件Mathematica的創造者史蒂芬·沃爾弗拉姆語)。學會放手,效果反而驚人。
孩子的大腦,也如一個剛剛初始化的大模型,有極大的參數空間等待優化。與其告訴他人生道理,不如給他精選的樣例,讓他通過自己的探索得到答案。這就是認知心理學家和教育心理學家傑羅姆·布魯納在其經典著作《教育過程》中提出的範例教學,又稱歸納式教學。
在數學教學中,教師給出一系列完整解題步驟的例題,學生通過分析示例主動理解數學概念和方法,而不是教師直接講解抽象的數學公式;在語文教學中,教師讓學生通過反復接觸大量語言樣例歸納語法規則,而非直接灌輸語法規則。這種方法不僅能加深理解,還更易於將其遷移到新的問題或情境中。
所以,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碰到的每一個難題,都不妨看作一次有意義的訓練樣例,父母無須立刻給出結論或答案,要讓孩子自己去觀察、體驗、比較、反思,從中找到自己的道。放棄說教,「給予註意,學會陪伴」,這才是養育孩子的黃金法則。

成人也是如此。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賦予我們的道理如同預訓練階段的基礎知識,它們在大腦中構建了認知的底層模型,卻不足以直接指導我們應對真實復雜的生活場景。生活真正考驗我們的是具體情境中的決策能力,而這種能力恰恰來自後續不斷的微調和強化學習。
例如,面對親密關系中的沖突,書上說「要理解對方,包容不同觀點」,但這樣的抽象道理並不能讓我們解決沖突;只有去傾聽、去表達、去調節情緒,然後根據對方的反饋微調和優化我們「人際交往專家模塊」的參數。所謂「紙上得來終覺淺,絕知此事要躬行」,這樣,我們才不會陷入「懂得了很多道理,依舊過不好這一生」的局部最優陷阱。
第三,註意也是遺忘。學習的本質,是對知識體系的優化。大模型像一個撿破爛的拾荒者,無差別地記憶所有接觸的信息。而人超越大模型的,是其所獨有的「選擇性遺忘」:有意識地強化對重要知識和場景的記憶,同時主動遺忘那些低效甚至有害的信息。所以,積極的遺忘並非失敗,而是一種認知優化的策略,它可以讓寶貴的註意力聚焦於那些真正有價值的信息和故事。《洛麗塔》的作者弗拉基米爾·納博科夫說:「你所領悟的人生真理,皆是你曾付出代價的往事。」
在學習過程中,選擇性遺忘就是「先做加法,再做減法」的思維模式。為策劃一個項目,我們會收集大量的信息,做大量的調研,努力將各種可能性都納入考慮範圍。這是必要的第一步,即先做加法。越接近決策階段,就越需要精準地做減法,選擇性遺忘。比如,關於一款新產品,我們最初想法無數:既要滿足市場需求,又要成本可控;既要功能強大,又要操作簡單;既想滿足年輕人的需求,又不願放棄中年人市場。但是,真正的產品設計者,要敢於主動「遺忘」那些充滿吸引力但幹擾產品核心定位的冗余信息,從而將註意力分配給真正的核心。設計師迪特·拉姆斯曾說:「好的設計不是堆砌更多的功能,而是敢於刪去多余的東西。」遺忘,也是註意力分配的藝術。
生活中,我們有時會情緒低落,這可能是因為過去一些不愉快的經歷:或許是一次失敗的考試,一次刻骨銘心的分手,甚至是朋友無意中的傷害。這些不愉快持續侵占和消耗着我們的註意力,不斷地喚起痛苦的記憶,讓我們陷入「身在當下,心在過去」的困境而無法自拔。選擇性遺忘不是強迫忘記這些不愉快,或者逃避甚至否認它們曾經發生。選擇性遺忘是承認,是接納——承認它們確實已經發生,無法更改,接納它們曾給自己帶來的傷害。但是需要明白的是,它們並不必然定義我們現在以及未來的人生。
心理學家卡爾·榮格說:「我們無法改變過去的事實,但我們可以改變看待這些事實的態度。」只有當我們真正接納了這些痛苦的經歷,允許自己放下情緒上的執著與執念,過去的負面經歷才會與我們握手言和,逐漸淡去;唯有這樣,註意力才會回歸當下,回歸我們能掌控的事情上。於是,我們重獲內心的平靜與自由。
遺忘,既是告別,也是起航。
——本文摘編自《通用人工智能:認知、教育與生存方式的重構》
欄目主編:朱自奮
文字編輯:金久超
本文作者:劉嘉
圖片創作:客家頭條
清華教授教你如何跑贏AI:人類有限的註意力該如何分配?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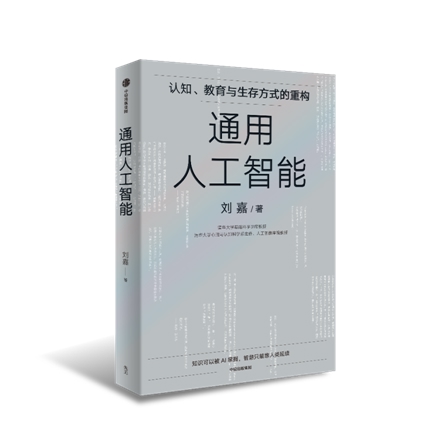
《通用人工智能:認知、教育與生存方式的重構》,劉嘉 著,中信出版集團出版
我們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智能躍遷。人工智能帶來的,遠不止於技術革新,更是一場深刻重塑人類認知、教育與生存方式的範式轉移。
這場躍遷的關鍵,不在於技術會走多遠,而在於人類如何重新認識自我。當知識不再稀缺,學習的意義何在?當智能無處不在,智慧的棲身之所又在何處?當工具變成智能體,人的核心價值又該如何彰顯?
清華大學基礎科學講席教授、清華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系主任劉嘉,站在歷史的交匯點,以獨特的跨學科視角,深入解析通用人工智能的演化路徑與底層邏輯、語言如何承載認知,以及人類能力結構如何在新時代被重新定義。
>>內文選讀
GPT的T,指的是Transformer,其最核心、最精妙之處就是「註意力機製」。它會對一段文本中每個詞語與其他所有詞語之間的關系進行評估,計算出它們之間的關聯強弱程度,從而捕捉信息之間的相互關系,以實現高效而精準的信息處理。所以,學習的本質也是註意力分配的藝術。
我們所處的世界彼此相連,而非孤立隨機。在物理層面,世界由物質和能量組成,它們之間不斷地相互作用,形成復雜而穩定的秩序。在生命層面,物種之間通過復雜的生態網絡連接起來,生態鏈中每個環節互依互存,任何個體的變化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。在人文社會層面,每個人看似獨立,但無時無刻不在通過溝通、情感聯結與社會網絡交織在一起。文明的存續與演化,來源於人與人之間頻繁而有序的互動。
英國詩人約翰·多恩說:「沒有人是一座孤島,可以自全……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損失,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,因此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,它就為你而鳴。」美國行為科學家阿莫斯·特沃斯基也說:「人不復雜,復雜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。」

應當如何分配註意力來認識我們所在的這個世界呢?
第一,註意高質量的數據和人。在機器學習領域,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第一性原理:「垃圾輸入,垃圾輸出。」再多的參數,再強大的算力,如果輸入的數據質量低下,最終訓練出來的大模型也必然表現糟糕。所以,OpenAI在訓練初期便嚴格把控數據質量,選用了維基百科、經典書籍、科研論文、優秀代碼和高質量互聯網內容作為註意力處理的信息。這些精心挑選的材料構成了GPT的認知基座。
截至2024年6月,我國短視頻用戶數量達到10.5億,占整體網民的95.5%,人均每天觀看時長約151分鐘。而閱讀用戶只有短視頻用戶的一半,人均每天閱讀時長只有23分鐘。AI在學習,人類卻在沈迷。
真正與註意力門當戶對的是高質量的數據集和人。在進入某個領域前,首先精心構建你的數據集:誰是這個領域的權威,哪些書、線上課程是這個領域的經典,哪些工具能讓這個領域的抽象知識變得具象清晰?之後,閱讀入門材料快速建立對這個領域的基本認知;接下來,對經典或權威的書籍或教材進行深度學習,建立完善的知識框架;最後,通過專業研究文獻並與專家或AI互動交流,拓寬和深化自己的認知邊界。
第二,註意實例而非規則。符號主義給AI以規則:「如果一個動物有尖尖的耳朵,胡須明顯,並且眼睛在夜間能反光,那麽它是貓。」這時,狐貍、猞猁、浣熊和狼也會被符號主義AI識別成貓。而聯結主義只給AI貓的圖片,各種各樣貓的圖片,讓註意力在海量的數據中主動探尋其中蘊含的模式和規律。前者是授人以魚——人類先提取特征,然後把特征餵給AI,即人類向AI輸入人類學習的結果,AI只需要記憶,正所謂前面有多少智能,背後就有多少人工。後者是授人以漁——沒有工程師總結的規則,只有精心挑選的實例,讓神經網絡自己學習,讓它自己去充分挖掘全部可能,因為「足夠大的神經網絡當然無所不能」(計算軟件Mathematica的創造者史蒂芬·沃爾弗拉姆語)。學會放手,效果反而驚人。
孩子的大腦,也如一個剛剛初始化的大模型,有極大的參數空間等待優化。與其告訴他人生道理,不如給他精選的樣例,讓他通過自己的探索得到答案。這就是認知心理學家和教育心理學家傑羅姆·布魯納在其經典著作《教育過程》中提出的範例教學,又稱歸納式教學。
在數學教學中,教師給出一系列完整解題步驟的例題,學生通過分析示例主動理解數學概念和方法,而不是教師直接講解抽象的數學公式;在語文教學中,教師讓學生通過反復接觸大量語言樣例歸納語法規則,而非直接灌輸語法規則。這種方法不僅能加深理解,還更易於將其遷移到新的問題或情境中。
所以,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碰到的每一個難題,都不妨看作一次有意義的訓練樣例,父母無須立刻給出結論或答案,要讓孩子自己去觀察、體驗、比較、反思,從中找到自己的道。放棄說教,「給予註意,學會陪伴」,這才是養育孩子的黃金法則。

成人也是如此。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賦予我們的道理如同預訓練階段的基礎知識,它們在大腦中構建了認知的底層模型,卻不足以直接指導我們應對真實復雜的生活場景。生活真正考驗我們的是具體情境中的決策能力,而這種能力恰恰來自後續不斷的微調和強化學習。
例如,面對親密關系中的沖突,書上說「要理解對方,包容不同觀點」,但這樣的抽象道理並不能讓我們解決沖突;只有去傾聽、去表達、去調節情緒,然後根據對方的反饋微調和優化我們「人際交往專家模塊」的參數。所謂「紙上得來終覺淺,絕知此事要躬行」,這樣,我們才不會陷入「懂得了很多道理,依舊過不好這一生」的局部最優陷阱。
第三,註意也是遺忘。學習的本質,是對知識體系的優化。大模型像一個撿破爛的拾荒者,無差別地記憶所有接觸的信息。而人超越大模型的,是其所獨有的「選擇性遺忘」:有意識地強化對重要知識和場景的記憶,同時主動遺忘那些低效甚至有害的信息。所以,積極的遺忘並非失敗,而是一種認知優化的策略,它可以讓寶貴的註意力聚焦於那些真正有價值的信息和故事。《洛麗塔》的作者弗拉基米爾·納博科夫說:「你所領悟的人生真理,皆是你曾付出代價的往事。」
在學習過程中,選擇性遺忘就是「先做加法,再做減法」的思維模式。為策劃一個項目,我們會收集大量的信息,做大量的調研,努力將各種可能性都納入考慮範圍。這是必要的第一步,即先做加法。越接近決策階段,就越需要精準地做減法,選擇性遺忘。比如,關於一款新產品,我們最初想法無數:既要滿足市場需求,又要成本可控;既要功能強大,又要操作簡單;既想滿足年輕人的需求,又不願放棄中年人市場。但是,真正的產品設計者,要敢於主動「遺忘」那些充滿吸引力但幹擾產品核心定位的冗余信息,從而將註意力分配給真正的核心。設計師迪特·拉姆斯曾說:「好的設計不是堆砌更多的功能,而是敢於刪去多余的東西。」遺忘,也是註意力分配的藝術。
生活中,我們有時會情緒低落,這可能是因為過去一些不愉快的經歷:或許是一次失敗的考試,一次刻骨銘心的分手,甚至是朋友無意中的傷害。這些不愉快持續侵占和消耗着我們的註意力,不斷地喚起痛苦的記憶,讓我們陷入「身在當下,心在過去」的困境而無法自拔。選擇性遺忘不是強迫忘記這些不愉快,或者逃避甚至否認它們曾經發生。選擇性遺忘是承認,是接納——承認它們確實已經發生,無法更改,接納它們曾給自己帶來的傷害。但是需要明白的是,它們並不必然定義我們現在以及未來的人生。
心理學家卡爾·榮格說:「我們無法改變過去的事實,但我們可以改變看待這些事實的態度。」只有當我們真正接納了這些痛苦的經歷,允許自己放下情緒上的執著與執念,過去的負面經歷才會與我們握手言和,逐漸淡去;唯有這樣,註意力才會回歸當下,回歸我們能掌控的事情上。於是,我們重獲內心的平靜與自由。
遺忘,既是告別,也是起航。
——本文摘編自《通用人工智能:認知、教育與生存方式的重構》
欄目主編:朱自奮
文字編輯:金久超
本文作者:劉嘉
圖片創作:客家頭條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